萧红《呼兰河传》“如果没法忘记他,就允许自己偶尔想念。真正的放下不是不再想起,而是想起时不再难过,谈起他时不再有情绪。”
如果没有办法将他从你的记忆中抹掉,你也可以偶尔地想念起这个人,毕竟真正的放下并不是不再想他,而是在想起他的时候,心中不再泛起任何的情绪。
关于这一点,萧红在《呼兰河传》里,也常常想起自己在家乡的那些事。
这些故事,都在时间的打磨之下,成为了情感的鹅卵石,并非是萧红遗忘了她,而是再度回忆起这些往事的时候,心中不再刺痛。
今天,博主从文学,心理学,社会学的角度,为大家从《呼兰河传》中寻找真正的放下是如何被诠释的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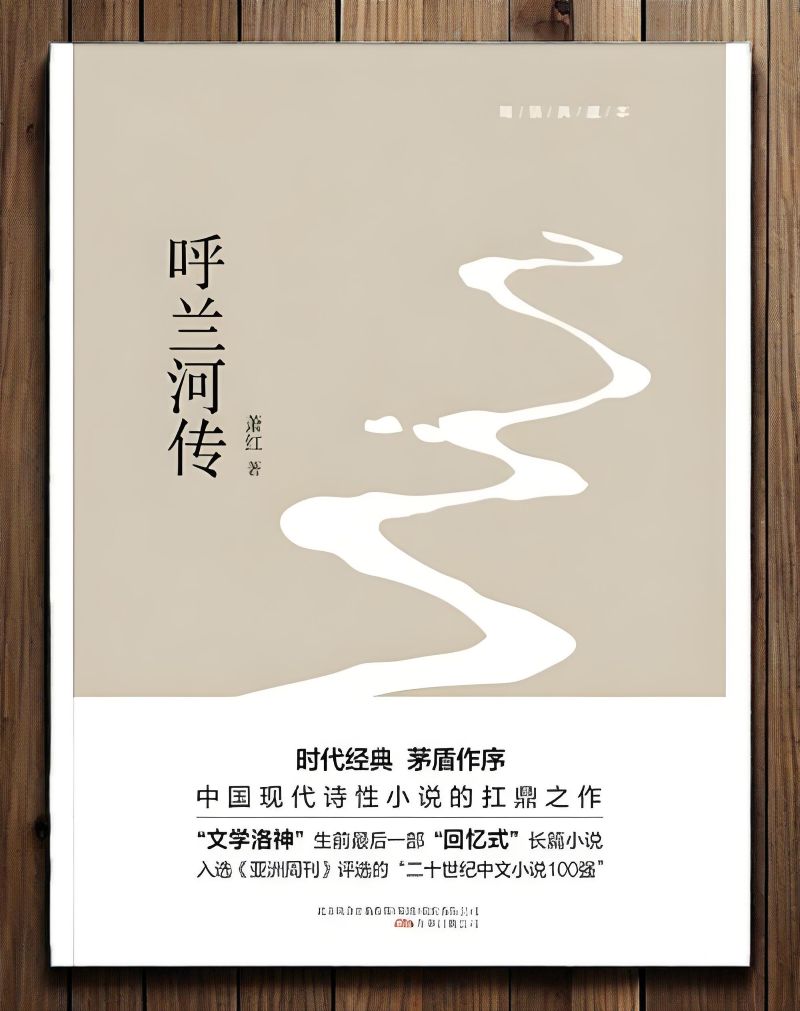
一,文学视角:童真滤镜下的创伤叙事
1. 孩子的眼睛,成人的哀伤
在《呼兰河传》这部小说中,作者用孩子的视角去看待她生活的环境,去看待她的周围人。
那些看似天真浪漫,充满童趣的语言背后,呈现出的却是成年人的世界中残酷的一面。
比如令人痛心疾首的小团圆媳妇的悲惨遭遇,一个年仅12岁的柔弱女孩竟然被婆家无情地对待最终失去生命。
更为令人叹息的是,在村民们的认知之中,仅仅将这一切当作是所谓“驱邪”行为导致的结果。
正是在孩子所具有的懵懂无知的观察视角,使得那些本就令人揪心的苦难,在被呈现出来时,显得更加荒诞不经且刺痛人心。
那些看似美丽动人的贝壳之中,究竟隐匿着多少象征着死亡的细微沙粒,只是这一切,似乎被那绚丽的外表给深深掩盖住了。
2. 冷笔写热泪,平淡藏惊雷
萧红冷峻的文字风格,以轻飘飘的方式呈现在书中。但是,这种看似轻柔的行文,竟在人们内心渐渐积成如同有着千钧之重的冰层。
就如她在写到祖父的死的时候,仅仅是以
“祖父死了,我就再没有走进后园”
这样简单的一句,没有嚎啕大哭,没有直白的怀念,却能够让读者从中体会出仿佛历经一生之久的那种孤独感。
这种“冷叙述”恰恰是文学上的高级处理:
“情感越克制,后劲越猛烈。”
3. 循环的时间,困住的人
生活在呼兰河的人们,长期以来都被一种称作“循环时间”的无形框架所困住。
比如,书中写到了跳大神,放河灯,看野太子戏等这类具有特定民间文化色彩,且在当地年复一年持续进行的活动。
这些活动事项构成了他们看似一成不变的生活轨迹,同时也在象征着,仿佛无论他们怎样努力都无法逃脱既定的命运。
然而,萧红却毅然决然地逃离自己的家乡,她用自己的行为打破了往日禁锢住他们的思想与生活。
但这就正如书中所说:
“呼兰河的人不是活着,而是在重复活着的姿势。”
二、心理学视角:记忆如何从荆棘变成苔藓
1. 创伤记忆的“去敏化”
在心理学领域当中,人对于痛苦的记忆往往会历经被称之为“去敏化”的这样一个过程。
去敏化的具体体现为,在经过了对痛苦的经历反复回忆之后,与之相关的情绪反应会呈现逐步衰减的态势。
而萧红在写《呼兰河传》的行为,从心理学角度来讲,她是将自己的内心所承载的痛苦,以文字的形式体现在纸张上,使这个痛苦能够暴露在阳光之下,最终让痛苦变得可以被触摸,被感知,从而减轻这种回忆上的痛苦感受。
作者的这种痛苦感受,在书中也有提及。
当冯歪嘴子那已然逝去的女人离世之后,他却依旧是以一种平静之态对孩子进行抚养,呈现出仿若“像什么都没发生过”的样子。
看起来,冯歪嘴子是麻木不仁的,实则是源自生存本能,即是以平静之态,抵御内心的痛苦。
这也在告诉我们:
“人必须学会与痛苦共存,否则就会被它吞噬。”
2. “安全距离”效应
萧红在写作《呼兰河传》的似乎,实际上早已阔别了呼兰河这片土地多年,因为有着时空上的间隔,使得她能够以一种较为冷静的视角去回望自己过去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活,而不至于被自己的情绪所淹没。
对于这种情绪,心理学上称之为“情感调节的安全距离”。
“当回忆不再带来疼痛的时候,人才算是真正的放下。”
这也正如一句话所说:
“记忆像一块冰,握得太紧会冻伤手,放在远处看,却成了风景。”
3. 未完成的哀悼
萧红的一生都处于漂泊的状态,呼兰河则是承载着她的诸多情感,同时也是永远无法真正回归的存在。
可以这么认为,于她短暂的漂泊的一生而言,呼兰河已经不是她传统意义上的故乡,而是她的“心理故乡”。
根据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所提出的观点,当人置身于面对失去这般状况的时候,唯有完成所谓“哀悼”这个过程,才具备继续维持生活下去的可能性。
按照这样的逻辑,《呼兰河传》就如同萧红所进行的哀悼仪式。
对于她自己而言,她写这部作品,不是为了将过往遗忘,反而是渴望自己能够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将故乡呼兰河融入到她的生命当中。
这也告诉我们:
“真正的放下,不是删除记忆,而是让记忆从伤口变成纹身。”
三、社会学视角:集体记忆下的个体挣扎
1. 乡土社会的“情感压抑”
呼兰河作为一个旧时中国乡土社会中典型的存在,在礼教与迷信这两种无形却强力的因素紧紧束缚之下,人们的情感处于被禁锢状态;
小团圆媳妇所遭遇的那一场令人痛心的悲剧,从本质意义上来说,实则是社会以一种极为隐蔽,且无人可确切察觉的方式对个体进行无情吞噬。
在这个过程当中,她的痛苦无人能够真正理解,而她最终走向死亡,也并未有人需要为之承担责任。
萧红将这个故事写了出来,是对这种“集体冷漠”的控诉,也是对个体情感的救赎。
所以,作者说:
“在呼兰河,一个人的悲剧只是别人的一场热闹。”
2. 女性记忆的“失语”与“复权”
萧红始终关注女性的命运。
在《呼兰河传》里,诸如祖母、母亲、小团圆媳妇以及王大姐等等这些女性所遭受的痛苦,竟然是以轻描淡写之态被呈现,甚至被认为她们的遭遇是理所当然的。
然而,萧红凭借其别具一格的写作方式,促使那些原本沉默着的记忆,能够重新获取并被听见。
书中这些女性的遭遇,在如今的社会中,也有些女性处于遭受着类似“被规训的记忆”般的境地。但无论怎样,“真正的治愈,是先允许痛苦存在。”
3. 现代人的呼兰河困境
今天的我们,是否也活在自己的“呼兰河”里?
职场PUA后,假装什么都没发生
失恋后强颜欢笑:“我早就不难过了”
原生家庭的伤,用“都过去了”掩盖
萧红的启示在于:
“逃避记忆的人,终将被记忆追逐。”
只有像她一样,诚实面对,才能让过去的灵魂安息。
结语:回忆的尽头,是温柔
在写完《呼兰河传》两年之后,年仅31岁的萧红在漂泊与病痛的折磨中,孤独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而在这部作品里面,那些往昔的记忆,被她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
它让我们明白到:
真正意义上的放下,不是彻底地遗忘过去,而是在偶尔的回想之时,不会再陷入往昔的那种难过情绪。
这一点,无论是对于故乡的回忆,还是对于初恋,对于前男友等的回忆,都是如此。
萧红也以她独特的笔触和情感表达,让我们产生了一种信念:
“雪化之后,泥土里会钻出新的芽。”
“人这一生,总要和某些记忆和解。
“不是因为它变好了,而是你,终于能在风雨中,为自己撑起一把伞。”




